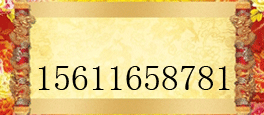浓情蛋炒饭
来源:亚欧能源网 发布时间:2018-05-28 14:50:28
母亲总说,真正的美食是“饿来香”,于是就总结出“小孩子吃饭挑食就让他饿着,饿到不行时随便做点什么都能吃个底朝天”的绝招。这一绝招曾经对小时候的我屡试不爽,如今被运用到两个小侄儿的身上,仍然百试百灵。其实小时候的我也并非真的饥不择食:不吃放姜末的菜、不吃糖油馅儿汤圆、不吃韭菜……于是往我爱吃的菜里放姜末,成了母亲对我不听话时的惩罚,这样反倒比棍棒伺候更能收敛我顽劣的脾性。
外婆就不一样,仿佛是为了弥补她女儿对我的“虐待”,对我近乎百依百顺,尤其是在“吃”这一让我最为感兴趣方面。 从小到大,外婆给我张罗过无数“香入脑髓”的美食,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忍不住大口大口地咽口水,仿佛那怡人的香味至今仍在鼻翼萦绕。童年里关于出自外婆那双巧手的美食记忆,最最深刻的,是每每酣畅的游戏或午睡后那一碗油光发亮的蛋炒饭。外婆做的蛋炒饭有与众不同之处:饭是玉米面做的粗粮,蛋是自养土鸡下的蛋,再加上她老人家绝妙的厨艺,堪比哈林歌里唱的“饭要粒粒分开、还要粘着蛋”。而我,常常是一大碗香喷喷的蛋炒饭下肚,就将上蹿下跳后的疲倦和莫名其妙的起床气远远地甩到九霄云外,瞳孔里只满满装着外婆那张慈祥的脸。
后来,我就像在外婆家院里亲手种下的那棵李子树,噌噌地高过外婆的肩头,再难像小时候那么逍遥地在她身边度过每个寒暑假。外婆做的蛋炒饭,成了我最馋最珍贵的美食记忆,偶尔能重温一两次那种妙不可言的感觉,都会恨不得将碗底舔出个窟窿。再后来,外婆患了眼睛胬肉和白内障,因为担心有风险而执意不肯做手术,基本靠听声音来辨认身边的人,更别说给我做蛋炒饭。因此,“外婆味”蛋炒饭成了一道让我魂牵梦绕的美味,化作我对外婆最绵甜悠长的依赖和眷恋。
就在我以为关于蛋炒饭的至美体验一去不回头的时候,某天科室领导送到工作现场的一碗蛋炒饭,竟让我吃出了久违的味道:“三大工程攻坚战”前方“战况”激烈,为了节约时间,一大早便赶往物资仓库进行材料收发,早餐被明目张胆地省略掉。就在几家施工单位的发料工作应接不暇,午饭也准备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地忽略的时候,主任经十几分钟车程特地送来一大碗温热的蛋炒饭,让我几乎当场泪崩。
当被关爱的感动、对蛋炒饭的怀念和妈妈的“饿来香理论”与现实的完美重合……一碗蛋炒饭吃得我无限感慨和无比满足,恨不得连自己的舌头也给吞下肚,吃完忍不住仔细检查一番,幸好碗底还完好无损,没有被我舔出窟窿。
“蛋炒饭,最简单也最困难,中国五千年,火的艺术就在这一盘……”一碗蛋炒饭,曾经被哈林唱成了一首歌,如今也被我吃成了一种道理:饭的味道,不在于它的配料和做的手法,而在于融进里面的心思和关爱。人与人之间不仅能锦上添花,还能雪中送炭的及时关怀;那份血浓于水、情浓于血的感情,才是人间珍味。(彭玫)
外婆就不一样,仿佛是为了弥补她女儿对我的“虐待”,对我近乎百依百顺,尤其是在“吃”这一让我最为感兴趣方面。 从小到大,外婆给我张罗过无数“香入脑髓”的美食,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忍不住大口大口地咽口水,仿佛那怡人的香味至今仍在鼻翼萦绕。童年里关于出自外婆那双巧手的美食记忆,最最深刻的,是每每酣畅的游戏或午睡后那一碗油光发亮的蛋炒饭。外婆做的蛋炒饭有与众不同之处:饭是玉米面做的粗粮,蛋是自养土鸡下的蛋,再加上她老人家绝妙的厨艺,堪比哈林歌里唱的“饭要粒粒分开、还要粘着蛋”。而我,常常是一大碗香喷喷的蛋炒饭下肚,就将上蹿下跳后的疲倦和莫名其妙的起床气远远地甩到九霄云外,瞳孔里只满满装着外婆那张慈祥的脸。
后来,我就像在外婆家院里亲手种下的那棵李子树,噌噌地高过外婆的肩头,再难像小时候那么逍遥地在她身边度过每个寒暑假。外婆做的蛋炒饭,成了我最馋最珍贵的美食记忆,偶尔能重温一两次那种妙不可言的感觉,都会恨不得将碗底舔出个窟窿。再后来,外婆患了眼睛胬肉和白内障,因为担心有风险而执意不肯做手术,基本靠听声音来辨认身边的人,更别说给我做蛋炒饭。因此,“外婆味”蛋炒饭成了一道让我魂牵梦绕的美味,化作我对外婆最绵甜悠长的依赖和眷恋。
就在我以为关于蛋炒饭的至美体验一去不回头的时候,某天科室领导送到工作现场的一碗蛋炒饭,竟让我吃出了久违的味道:“三大工程攻坚战”前方“战况”激烈,为了节约时间,一大早便赶往物资仓库进行材料收发,早餐被明目张胆地省略掉。就在几家施工单位的发料工作应接不暇,午饭也准备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地忽略的时候,主任经十几分钟车程特地送来一大碗温热的蛋炒饭,让我几乎当场泪崩。
当被关爱的感动、对蛋炒饭的怀念和妈妈的“饿来香理论”与现实的完美重合……一碗蛋炒饭吃得我无限感慨和无比满足,恨不得连自己的舌头也给吞下肚,吃完忍不住仔细检查一番,幸好碗底还完好无损,没有被我舔出窟窿。
“蛋炒饭,最简单也最困难,中国五千年,火的艺术就在这一盘……”一碗蛋炒饭,曾经被哈林唱成了一首歌,如今也被我吃成了一种道理:饭的味道,不在于它的配料和做的手法,而在于融进里面的心思和关爱。人与人之间不仅能锦上添花,还能雪中送炭的及时关怀;那份血浓于水、情浓于血的感情,才是人间珍味。(彭玫)
政策解读
能源人物
能源装备
亚欧能源网 广告热线:010-61224401 传真 010- 61224401
客服QQ:924467170 Email: mxzh2008@163.com Copyright
2005-2011 aeenets.com
All Rights Reserved. 亚欧能源网 版权所有 备案编号: 京ICP备12037512
本站网络实名:亚欧能源网